【成御】DOG PARK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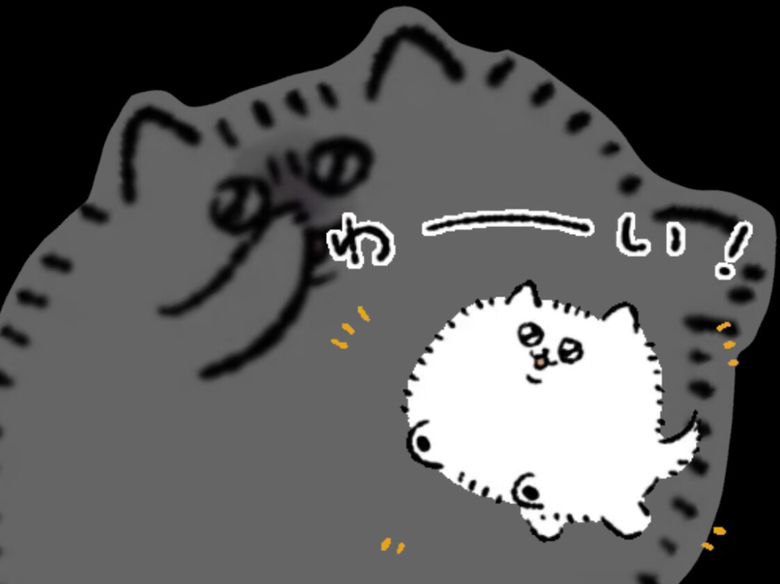
一块看起来陈旧而油腻的红色牌子上写着两个英文单词:
DOG PARKING。
牌子的下面,贴心地凸起了数个挂钩状事物,有高有低,错落分布,上面悬挂着色彩与材质各异的绳索,有长有短,参差不齐。绳索的另一端,连接着几只体型、毛色、样貌皆不相同的动物——这并不奇怪,在这个号称种族熔炉的自由国度,你可以在同一个房间里看到若无其事杂处的各种毛色、肤色、种族的动物,而人们并不以为怪——它们或坐或站,有些焦急,有些低落,有些则显得呆滞愚蠢,它们之间本可以聊聊天,交换一下自己独特的气味,炫耀一下自己心爱的颈圈,不过很可惜,它们好像并没有那样的心情。
它们是狗。因被禁止进入快餐店而被主人临时寄存于“DOG PARKING”的狗。
在以人类为主导的社会中,狗并不是在任何场合都受到欢迎的,尤其当是它们随时可能大吵大闹并夺走隔壁用餐的人类孩童的汉堡时。不过,在DOG PARKING,并不是所有的狗都是因为缺乏礼貌而被寄存的,也可能是它们的主人不想携带一个缺乏自理能力的大号的麻烦制造者。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狗都戴项圈和狗链。
比如,那只角落里的白色博美犬。
它洁白、蓬松、傲慢,有着华丽的领毛,尽管这让它看起来缺少颈部,像一个球。它还没有蹲踞在一旁的拉布拉多的脑袋大,但它有着别样的自信,始终高扬着头,仿佛奉行着优雅礼貌的处事原则,但如果真要动武,它也不会惧怕任何狗。它没有佩戴项圈,也不是被拴在DOG PARKING的,比起它垂头丧气、仿佛被遗弃的同类们,它更像是一个傲慢的观察者,打量着快餐店中的每一个动物,看起来气定神闲,就如同在等待服务员递给它属于自己的儿童套餐。
虽说它的神态始终矜持而优雅,但眼神中的嫌弃和敌视是藏不住的。就比如,每当拉布拉多发出略显粗重的呼吸声,它总是露出苛责的眼神;再比如,坐在拉布拉多旁边的那条狗,无论他在做什么,傲慢的博美犬都会用不友善的眼神打量他,他的存在似乎就触犯了博美犬的审美——庞大、粗糙、灰扑扑、坐姿粗鲁随意、眼神颓废无神、缺乏柔软的长毛,最主要的是,他也像博美犬一样,脖子上没有一条项圈!
哦不!这好像不是一只狗,而是一个同样被寄存在DOG PARKING的男性人类!
男人穿着旧到分辨不出原本颜色的卫衣,头戴一顶品味一言难尽的冷帽,脚踩一双肮脏破旧的拖鞋,顶着半张脸上稀疏的胡茬,一时令人难以说清,街对面的流浪汉是否比他要更体面些。这似乎是一个亚裔男性,在这座城市里也不算少见,他个子不算高,身材中等,看起来有三十多岁或者更老,长相几乎让人说不出任何特点,那身油腻的打扮,在这家以平民为主要受众的廉价快餐店里,就像将一尾沙丁鱼放进了海岸中,彻底地融入了,就算大大咧咧地坐在群狗之中,也毫不违和。
在他周围,热浪裹挟着廉价油脂的味道不断卷来,香烟气味缭绕其中,粗鲁的谈笑声、肮脏的叱骂声不绝于耳,人类的声音和味道充斥在这小小的只有四五张桌的快餐店,柜台后之后一个服务生带着不耐烦的神情忙碌着。油腻模糊的玻璃门外,是荒凉的公路,已被磨光了或黄或白的标识,时有蓬草飘过,比破旧越野车的路过还要频繁。像这样的肮脏的角落,在这座可称藏污纳垢的都市之中还有成千上万,真正自恃身份的绅士是不会造访这样所在的,而这个穿着灰色帽衫的男人却可以,他像是为了穿梭于不见光的肮脏角落而生,就算他翻弄街对面那个肮脏的垃圾桶,从中捡走点什么,也不会有人多看他一眼,更不会有人记住他来过。他就是有一层在这种所在如鱼得水的保护色。
但此刻,他也被人寄存在了DOG PARKING,很显然,“饲主”短暂地用不上这条油滑的狗。
目前,他正身体歪斜地靠在龟裂脱皮的皮质椅背上,好像同时被抽走了脊柱与生命力的脱水面条鱼,他没精打采的表情与旁边两颊皮肉下垂的拉布拉多别无二致。与拉布拉多不同的是,他正百无聊赖地将手边的一包薯条中的每一根裹满番茄酱,送入口中咀嚼,似乎聊以此作为消遣。说来也怪,自从摆弄手机作为一种娱乐在人类之间普及后,就很少再见到这样无聊的人了。
气氛十分沉闷,男人无所事事地吃了一会,仰头看了一会沾满油渍的天花板,在眼皮打架之前,又低下头吃起来。带有亚裔特征的黑眼睛始终半睁着,没有聚焦,在他脚边不到两码的地方,隐约有一团白色的小东西正蹦跶着对他龇牙咧嘴,但因为那团白色太小了,并没有成功映入他的眼帘。不过很快,他注意到了身边的拉布拉多正用夹杂些许幽怨的眼神呆呆地看着他,目送每一根沾满番茄酱的薯条进入他的口腔。他微一挑眉,扬了扬手边那包薯条,用听起来语调刻意而生硬的美式英语问道:
“你想吃?”
“汪。”
拉布拉多作出了回答。
傲慢的博美犬终于将头扭向一边了,男人和拉布拉多都不知道的是,它很讨厌番茄酱,认为那种东西缺乏品位,尽管根本没人在乎它的看法。或许它也因此明白了男人被“饲主”寄存在DOG PARKING的原因——他的英语真的很烂,又不能熟练地使用电子设备,放任他四处走动,肯定会制造麻烦,而将他带在身边,又太累赘了。这就是饲养大型犬的显著缺点。
男人将一根体贴地裹好了番茄酱的薯条送入拉布拉多的口中,很快又裹好下一根,喂给自己,就这样和淡黄色皮毛的大狗交替地吃起薯条。他很大方,自来熟,毫不拘束。不知道是不是同病相怜的狗之间更容易产生友谊,男人与拉布拉多之间的氛围和谐极了,或许如果男人的英语再熟练些,他们还能聊得更投机,而现在他们只能一起观看破烂的小电视屏幕上循环播放的无聊广告,那广告恰好就是宣传某个品牌的廉价番茄酱的。
正当他出神地看着电视屏幕上跳舞的番茄酱时,却有一道阴影逐渐地投了下来,不乏压迫感地,将那男人平凡的身形笼罩在其中。过了几秒,男人似乎才迟钝地意识到,有一个人站在他的身边,正在默不作声地看着他,并报以没精打采的狐疑眼神。来者是一名彪形大汉,面相酷似蹲在他身边不远的一只法国斗牛犬,穿着一身风尘仆仆的破夹克,眉角上有一道凸起的疤痕。如果美国传统词典打算给每一个词条配一张插图,他的脸刚好适合被放在“恶棍”这个词下面。不管他的来意是什么,一个惶恐不安的外地人都该被这魁梧的身材与满脸的横肉恐吓到,进而答应他的所有要求,而他今天好像碰上了个迟钝的蠢货,不但隔了好几秒才意识到他的存在,看到他后还只是轻轻一挑形状奇怪的眉毛,连坐姿都没有一点改变,这让他对面前这个黄种人矮子颇为不爽,不过好在,这条东洋土狗马上就要成为他们手中任人宰割的羔羊了。
想到这里,他干裂的嘴角不禁咧开一个残忍的笑容,迎着那人狐疑的目光,挥了挥手中的一叠扑克牌,用西部口音明显的英语说:
“你好像很无聊,兄弟。”
“玩牌吗?德州。只用筹码不用钱的那种。”
亚裔男人眼中的狐疑并没有立刻消散,仍旧不解地打量着来者不善的彪形大汉,原因无他,他听不懂这人在说什么。然而很快,他看到了来人手中,那叠带着轻微折痕的扑克,茫然的脸上逐渐绽出了笑容。
他虽说听不懂英文,却认得扑克以及上面的花色和数字,再也没有比这更有效的沟通了。
他友善地笑着说:
“那很好。”
就好像他听懂了来人说的话一般。
而有一个很明显的事实——至少这个男人会打德州。
很快,他离开了DOG PARKING,坐到了角落里不起眼的一桌,这一桌上坐着几个相貌丑陋的男人,比DOG PARKING 更像是座动物园。他们彼此熟识,桌上摆着几叠破旧的纸牌和堆积成山的写在纸上的简陋筹码,墙上贴着破损严重、已经看不出原本样子就旧海报,和已经被焦油与尼古丁熏黑的“禁止吸烟”的警示标语。这伙人看上去经常坐在这里,服务生对此已经见怪不怪,不过也终究不敢招惹、驱赶,其他顾客看上去也对他们心怀忌惮,都坐得远远的。
穿灰色帽衫的男人却似看不见这些,在彪形大汉的引荐下,从容地坐到他们之间,熟练地抓过筹码和手牌,和他蹩脚的英语不同,他的神态自若得就好像这堆牌是他准备在这里的一样。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作为这群恶棍之中的弱势者,他很和善地对桌上的每一个陌生人笑着点头,桌上人也对他笑,只不过一方的笑容中带着掩饰不住的狡黠与残忍,另一方的笑容却是那样纯良无害。
笑容不会消失,它们只会从一个人的脸上转移到另一个人的脸上。一刻钟后,一方带着的残忍笑容逐渐消失,而纯良无害的那一方更加悠然自得、老神在在。与此相伴的是,桌上原本分散的纸筹码,也都逐渐在其中一人的面前堆积成山了。
毫无疑问地,筹码汇集到了那个穿灰色帽衫的男人面前。
此刻,他正用略显粗糙的拇指与食指,漫不经心地摩挲着生满胡茬的圆润下颌,像个彻头彻尾的外行人一样,摆弄观察着手里的手牌,看起来仍然没什么精神,但较刚刚呆坐于DOG PARKING时,显然并没有那么无聊了。他打牌很快,和很多不假思索的新手一样,新手往往不会记牌、不懂猜牌,也不讲究那些尔虞我诈的心理战术,玩的主要是牌桌上的热闹氛围,因此乱打一气也无可厚非,可是不知为什么,面前这个长相普通的男人也是随手的摸牌、看牌、弃牌,看似毫无逻辑与套路,押注也全凭心情:时而局面一片大好,他却弃牌,宁可损失上一两个盲注;而有时明明是凶险万分、毫无胜算的局面,他却一再诈唬似地加注,最终将满桌筹码都收拢到手边。
那些原本坐在桌上的恶棍,脸色都变得奇差无比,额头也浸出了冷汗,险些掩饰不住眼中的恶意,再不是最初自信满满的样子了。可是面对这个男人,他们却毫无办法,只能用眼神彼此埋怨,就好像是同伙坏了自己的好事一般。
终于,牌桌上再次呈现了一边倒的局面,帽衫男人手里攥着一把同花顺,看起来只要他继续不假思索地加注,就能一举将桌上所有筹码收入囊中,成为最后的赢家。
桌上短暂地寂静了,再没有一个人说话,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到帽衫男人的身上,怀揣着残忍的期待,嘴角慢慢上翘,像是久违地找到了些许学生时代布下捉弄老师的陷阱之后那兴奋的感觉。而那个灰扑扑的男人继续着无动于衷和迟钝,像是对众人的目光毫无所觉,看了看手中的牌,又看了看一众对他怀揣期待的牌友,最后看了看被焦油熏黑的天花板,似乎在这短短五秒之中,进行了一次无济于事的思考,最终意识到了自己根本不懂牌术的事实,于是放弃思考,露出单纯的微笑道:
“FOLD.”
他又弃牌了,将手中的同花顺扔到了桌面上,好像扔掉了一个困扰着他的包袱一样,笑得很坦率。
然而,桌上那些恶棍的表情全部凝固了。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骗局专门半强迫地“邀请”无知的外地人加入,起初给他们些甜头,让他们赢上几局,等到手中的筹码积累得越垒越高,一般人都会丧失谨慎的品格,变得鲁莽草率,这时一个小小的圈套便能让他们输光底注。这些无赖恶棍对于这一勾当早已熟练,配合得当,能够用简陋的千术模拟各种牌型,眼前的这一种便是其中最险恶之一,手中握着一把同花顺,又有谁会直接弃牌?多半会想方设法为自己多争取些利益,而他很快会发现,无论自己做出什么选择,最后都会输光好不容易得来的全部筹码,因为这根本就是一个陷阱。输光筹码后,尽管那个邀请他的彪形大汉承诺过“只玩筹码不玩钱”,当那些不怀好心的恶棍带着残忍的笑容围上来时,无论是谁都得乖乖交出钱包以免皮肉之苦。
然而这些已成惯犯的无赖恶棍今天第一次遇见了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男人。
他明明有着令人不忍直视的英语水平,却熟练地说着德州扑克的术语,就像是有着幸运女神的眷顾,每次不看底牌地加注和弃牌,都恰好吞掉了他们的诱饵,却躲过了诱饵背后危险的铁钩,就这样一直赢到了最后!
这是最大的挑衅。他们确信,这个男人有极大可能是装模作样来砸场子的同行,不知用了什么手段,残忍地戏耍了他们!
此时,气氛已经凝重到了极点,所有人面色不善地盯着那帽衫男人,像是将欲扑击的兽群发出威胁的低鸣,在那恐怖的低气压之下,就连周围不相关的顾客也发现了祸事的苗头,他们也脸现忌惮,一边偷偷地将视线投向这边,猜测着是哪个大胆的愣头青敢于招惹这群地头蛇,一边不动声色地远离低气压的中心,生怕将祸水惹向自己。
那位于风暴中心帽衫男人也终于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了什么,他依旧镇定,却把懵懂和善的笑意收敛了些,颇有几分无可奈何地看了看两旁带着不加掩饰的恶意的恶棍。
自那些人不善的眼神,他知道自己已经被当成了出千耍诈、故意挑衅的同行了。他的无可奈何是那样真切,简直想要把自己的心脏剖开来给这些人看看——这些智商有限的牌友,打出每一套牌时,都把底牌在脸上写得一清二楚,哪次是诱饵跟注,哪次是陷阱需要弃牌,直白明显得如同白天里的太阳,平心而论,他赢这些人,还有必要出千耍诈吗?不!他几乎连自己的牌都不用看!
他在心中深深叹了口气,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座中几人的身量和拳头大小,紧急思索着等下如果真的动起手来,如何毫无形象地躲闪以避免鼻骨骨折的命运。
他本穷极无聊,想见识见识异国他乡的千术,谁知这乡野不毛之地的骗术比他想象中有简单效得多,核心精髓就在于,拳头硬。
他不禁无奈地想,那个男人说得对,自己就是不惹事事惹人的命,只适合待在DOG PARKING,和狗坐一桌。
“喂。”
他听到之前那个“邀请”他加入牌局的彪形大汉低沉地叫了他一声,他嘴角带着有几分僵硬的笑,回望向对方。
“你是不是出千了?”
大汉不善的面色逐渐转为冷笑,此话一出,整个餐厅的空气都仿佛降低了两度,所有人的目光都明里暗里投了过来,就连那柜台后心不在焉的服务生也偷偷探出头查看,他们或是暗怀期待,或是忧心忡忡,但都知道,这句话是一个信号,不管出千的罪名是否为莫须有,在这些恶棍的恼羞成怒之下,总会发生点什么了。
伴随着恶棍那张神似法国斗牛犬的巨脸靠近,一股浓郁的烟臭喷吐到帽衫男人的脸上,顿时使他喉头一紧。他很厌恶烟味,在地下牌桌边闻得已经够多了。他嘴角蠕动了一下,才强行压抑下干呕的冲动。
“你……是不是出千了?!”
没有得到目标的回复,恶棍的恼羞成怒抵达了新的顶峰,咬着后牙,带着不加掩饰的威胁意味,一个词一个词地重复了刚才的质问,却看到帽衫男人对他露出一抹若无其事的和善微笑,拿起手边翻滚着冰块的冰水,气定神闲地喝了一口。
那个男人听不懂。
对他来说,听不懂又无从解释的情况下,只能尽量友善地微笑了。毕竟伸手不打笑脸人……
可下一秒,伴随着塑料椅翻倒与玻璃杯破碎的剧烈响声,那恶棍毫无征兆地站起发难,一把攥住男人宽松的帽衫领口,他壮硕的身形提起这个身高平平的东亚男人不会比提起一只大狗更费力,因为极度的难度,他的脸颊涨得紫红,五官狰狞地蠕动着,嘴角比鼻翼不断抽搐。他丑陋而智商低下的脸着实有着不低的冲击力,帽衫男人瞥了眼自己脚边那已成前车之鉴的粉身碎骨的玻璃杯,依旧镇定自若地笑着,双手举到与面部平齐,似在防备着攻向面门的拳头,更像在用国际通用的肢体语言举手投降。
气氛顿时紧张到了极点,像是一桶高温下的火药,只需要一个火星便能点燃。所有人都几乎确定,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异乡人今天一定要吃点苦头了。
就在这时,极端的寂静里,悬挂与门口的破旧感应器,不合时宜地发出了一声走音变调的“欢迎光临”,顿时给这紧张的气氛平添了几分荒诞滑稽。在场的所有目光都不由自主地投向了门口,就连DOG PARKING中的犬只都扭头看向了来人。
那是一个高大挺拔的身影,背对着玻璃门外阳光炽烈的公路,看不清面容,只显露出身着笔挺长风衣的身影。人们这才注意到,这荒僻郊外的破烂快餐店门外,听着一肆意张扬辆张扬的大红色跑车,眼光下闪着一尘不染的金钱的光辉。
那个穿风衣的男人有一张冷峻深刻的面容,佩戴着一副严肃刻板的黑框眼镜,他向前迈了两步,清脆而强硬的皮鞋硬跟声便响了两下,但他也只往前走了两步,像是不屑于让黏腻的地面污染他明亮精美的皮鞋。
而这两步也脱离了背光的状态,足够快餐店中的所有人看清他的样子。
整洁笔挺、没有一条多余褶皱的西装风衣,宽阔挺拔的肩背,令人又畏又恨的隐隐透露着傲慢的眼神,还有胸前洁白如花朵般绽放的繁复领花。就连品味苛刻的博美犬都忍不住多了这男人华丽的领巾与线条优美的胸脯两眼,自己的头也不知不觉昂得更好了。
这个男人看起来既昂贵又严厉,习惯于出没于这些肮脏廉价处所的,无论是人还是狗,他们屈居人下惯了,对于堕落是那样的麻木,却对另一种人有些极其敏锐的嗅觉。
那种人,早些年是他们要叫“老爷”的人,如今是他们要叫“长官”的人。那种人,是在这个阶层划分明显的国度中,站在金字塔上方执着鞭子的人,再说得简单点,是上等人!
眼前这个穿红风衣打白领巾的男人无疑是个“上等人”,在父权主导的社会中,将握着最直白的权力与权威。他的出现让那些恶棍敏锐地感受到了威胁——那是一种野狗在被套上电击项圈前感受到的威胁——纷纷将警惕的目光投向那来者不善的男人,就连握着帽衫男人衣领的手都不自觉地放松了。
男人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斯文严谨地推了下黑框眼镜,只淡淡地瞟了眼DOG PARKING,便确认自己要找的人不在那个角落。这个小小的快餐店在这个男人锐利如鹰隼的目光下就像一池清澈的水洼,其中有几只龟几条蛇都一目了然。他立刻注意到了另一个角落中一触即发的危险局面,看到了打翻在地上的椅子和玻璃杯,看到了桌上的堆满的扑克和筹码。他依旧没有任何表情。
但当他锐利冰冷的目光扫过那些恶棍的身上时,他们纷纷感受到一股电流蹿过皮肤的酥麻感——那是一种几乎凝为实质的危险预感,是小鼠见到毒蛇,是毒蛇见到鹰隼,是任何动物见到他们命中注定的掠食者,是一切罪恶见到他们的克星。
他们都看到了,那个男人一边手臂上围着一枚臂章——那是监察局特别调查员的臂章。
为首的恶棍终于松开了攥着面前人领子的手。只有那个刚才还处在绝对下风帽衫男人露出了一个发自内心的笑容。
“你在干什么?”
来者用清晰而优雅的英语问。
“该走了。”
他的语气无比平淡,几乎听不出任何情绪的波动,就好像没看到角落里这一幕闹剧一般。伴随着句酷似命令的话语,他转身便走,风衣下摆掀起一个优美的弧度,只留下一个轮廓线条干脆利落的背影。每一个人,每一条狗都齐齐转头,目送着他,只有帽衫男人的笑容愈发灿烂了。
“该死。”
那恶棍低声斥骂了一句,他还想重新去抓那惹恼了他的东亚男人的衣领,有心给他点颜色瞧瞧,但刚才进门的那个“上等人”带给他的压迫感实在是太强烈了,他的双手现在还残留着颤抖的感觉。
“该死……”
他又骂了一句,看到那帽衫男人整了整衣领,朝他笑着摆了摆手,像是礼貌的告别,却又是货真价实的挑衅。他三步并作两步,赶在那红色风衣的绅士推门出去之前,谄媚地跟在他身后,毫无尊严地摇着尾巴,竟好似将一条无形的狗链递到那男人的手中一般。
他在炫耀。
在场的任何一人或任何一狗都能够感受到,这个男人令人火大的脸凑成了一个炫耀的笑容,就好像在向所有人宣告,看吧,我是这位尊贵先生的狗,你们又能奈我何?打我之前总要看“主人”吧!
所有恶棍都将后牙咬得咯吱作响,其他顾客则不忍直视地移开了实现,只有那些被寄存在FOG PARKING的狗,眼神中隐约透露出艳羡的神色。
只有狗懂得,有时候,当狗是一种享受的体验。
而那红色风衣的男人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一眼,没做任何表示,他笑容中的“享受”就已经无法掩饰了。
终于,他们推门而出,跨上了停于门口的那辆飞扬跋扈的座驾,伴随着轰鸣的马达声与扬起的尘土扬长而去。
拉布拉多还在等他的主人,没了帽衫男人的帮助,它吃不上蘸番茄酱的薯条了,只能掀起松垮的眼皮,怔怔看着电视上循环播放的番茄酱广告。一旁的博美犬将一切都看在眼里,它将目光从油腻的玻璃门处移开,样子好像在考虑,是否要把今天的所见所闻写进博客。
十分钟后,警车的鸣笛声响起,几名陌生的警官从车上下来逮捕了那几个恶棍。诈骗、非法赌博、寻衅滋事的罪名叠加,足够他们在拘留所内喝上一壶。
那位偶然降临这乡野之地的大人物虽不屑于和这些稷蜂社鼠一般计较,但威胁了他的狗,还是总要付出些代价的。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