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御】专业怪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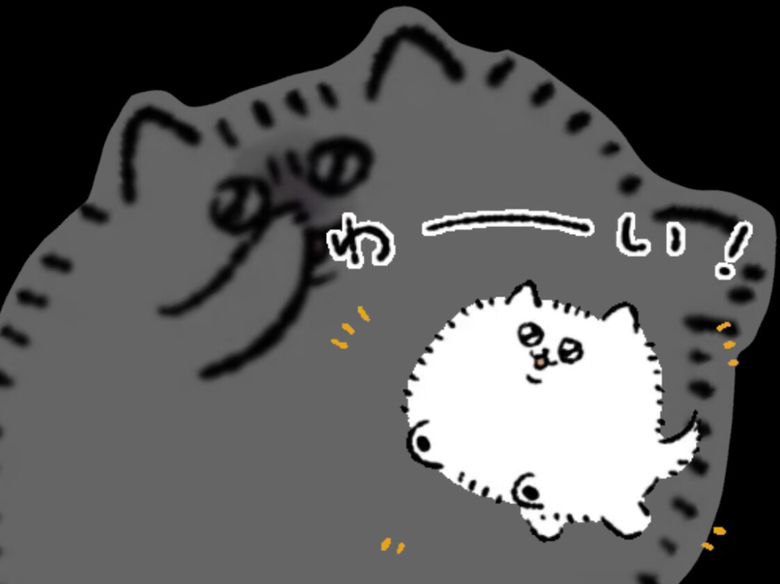
*轻微的双方非人类表现注意
*可能存在轻微恐怖/猎奇/血腥
△▽
“弟弟……”
寂静而漆黑的房间。
“弟……弟弟…………”
躺在被褥之间的男人缓缓睁开了眼睛,他感到,寒冷像是一种液体,缓缓将他身上的这床被子浸透了。
有人在说话。
“弟弟,你冷吗?”
是一个男孩的声音,颤抖的,虚弱的,原本声如蚊讷,断续而不成言,逐渐地也说出一整句话来了。
男人浑身开始战栗起来,被子像是浸透满冰冷黏腻到极点的液体,死死压在他身上,使他动弹不得。
“哥哥……你呢……也……冷吧……”
另一个声音响起,是一个听上去更小的孩子,也更加细弱。
男人终于听清了,他的双眼无声地瞪大。那两个孩子声音不来自房间中的任何一个黑暗的角落,就来自他身上所盖的这床棉被之中。
“弟弟,你冷吗?”
声音再次出现。原本断断续续的话语,终于变得越来越清晰,仿佛此时此刻正有两个孩童在那床棉被中对话一般。
那男人的面孔因恐惧而变得扭曲起来,他努力想要活动四肢掀开被子,可那床被子就如同一团黏稠的血肉一般,蠕动着,将他裹得越来越紧。他想要惊声尖叫,可是却像是被黑暗死死捂住了嘴巴,连呼吸都变得困难。
“哥哥,你呢?也冷吧?”
另一个幼儿的声音开始变得尖锐起来。
好冷……
男人的整个身体都剧烈地颤抖起来,他感到一种彻骨的寒冷正在缓慢地渗入身体,沿着他的血管爬行。整个房间冷得如同一个巨大的冰窟。
他这才想起来,现在本是七月,他住在这家以古朴为卖点的带庭院民宿之中,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彻骨的寒凉?!
“弟弟,你冷吗?”
“哥哥,你呢?也冷吧?”
两个孩童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凄厉,就像是被挖去眼珠的猫,重复着这两句问题。男人的呼吸急促,拼命地摇着头,恐惧的泪水充斥着他的双眼,他感到那寒冷忽然飞快得像他心脏逼去。
“弟弟,你冷吗?!”
“哥哥,你呢??也冷吧?!”
那声音听起来再也不像是什么幼童,而是凄厉得犹如一百只有着长而尖锐的指甲的手在疯狂地抓挠着玻璃。房间内两侧纸糊的拉门呼啦啦地响着,黑暗如同一只暴怒的巨兽,在看不见的虚空中翻滚沸腾着。
要死了……
男人死死瞪着眼,绝望的泪水顺着几欲渗出鲜血的眼角滚滚而下,他喉咙中发出不似人类的嗬嗬声,肺腔如同一个残破的风箱。
真的……要死了……
他一片空白的脑海之中,迟缓地浮现出这个想法。
他早该知道的,那些关于这家旅馆的恐怖传闻都是真的,听说店老板为了打造逼真的复古效果,店内许多陈设都是货真价实的古物,在其中,说不定就有哪一件上面带着可怕的诅咒。
他不该来的……他想,可是,已经晚了。
“弟…………冷……嗬……嗬呃啊啊啊啊啊啊……!!”
声音彻底变成可怕的尖啸,漆黑的空气像是无数只手,死死将他扼住,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快要被挤爆了,浑身的骨骼和血管都发出即将爆裂的呻吟。眼球周围破裂的血管涌出鲜血,濡湿了他的枕头。他就要死了,寒冷已经攥住了他的心脏,他感到灵魂快被拉扯出肉体,白色的霜像是霉菌一样迅速覆盖了他的脸,眼角流出的鲜血冻结了,他浑身都皮肤都显露出一种将死之人的青紫色。
他就要死了,临死之前,甚至都没能发出一声呼救。
他意识模糊,瞳孔逐渐涣散,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凝结着,已经在等待死亡。这样模糊的痛苦持续了不知多久,他的灵魂颤抖着徘徊在死亡的边缘。
忽然,他的眼球动了动,一丝神智回到了他的头脑之中。
他好像听到了一个声音。
“七月炎炎夏,飞书显花押……”
那是一段歌声。
“竹林朝露化黄花……”
那竟是一个男人的歌声,由远及近,自靠近走廊的那个方向传来。这种仿古旅店建筑,四面墙壁都是由木质结构和可以活动的纸拉门组成,故而走廊外的声音能够异常清晰地传入他的耳朵。
除去歌声之外,还有一个脚步声。
哒……哒……那是硬质的鞋跟踩上木地板的声音,听上去颇为悠闲。
“奴念郞,于桥旁,心意如白霜……”
那歌声还在继续着。声音不甚大,却十分悠扬。
那虽是个男人的声音,唱着女人的曲子,却丝毫不忸怩,声音清澈,低回婉转,音韵缠绵之间,竟颇有婀娜幽怨之意,仿若一名妙龄少妇,在月色下凄凄楚楚地顾影自怜。
那个唱歌的男人越走越近,那从容悠闲的姿态,就如同在投入地扮演着曲调中那幽怨的女郎,不知不觉间,却有一股森森的鬼气自其中发散而出。
男人的瞳孔再次剧烈颤抖起来。
“此生何时还可诉情长……”
他想起来了,这首歌……这歌词……
他本就是一个喜欢从古代怪谈之中取材的恐怖小说作家,又怎么可能不知道这首歌。这是《杜若》,是那首传说之中过桥时无论如何也不能吟唱的歌曲,是一支“鬼谣”。古籍《雨月物语》里记载了它的唱词,可是曲调却早已经失传了,如今竟从这走廊里一个来历不明的神秘男人口中听到了如此活灵活现的演绎。
男人只觉得前所未有地头皮发麻。
不知何时,房间中那指甲抓挠玻璃一般的尖啸声竟也消失了,房间中的黑暗就像死了一般凝固,就如同,连那不知名的可怕怪物也在屏息细听那歌声。
“七月炎炎夏,飞书显花押……”
可是,这一唱段结束,那男声似乎便唱不出下一段,转而如同一台老旧的录音机,忘我地重复着这几句。
房间内的黑暗似乎焦虑地蠕动起来,像是一团蠕动的毛发和血肉,散发着冰冷的腥臭。
“竹林朝露化黄花……”
不知不觉,脚步声已走至隔间附近。男人的心脏剧烈跳动着,他迟钝地意识到,自己的生或死,或许,便要决定在那一瞬间了。
近了,近了……
男人瞪着已经眦裂的双眼,死死地盯着那一扇纸糊的拉门。他知道,走廊里有月光,那唱歌之人走过,定会在上面留下模糊的影像。
房间之中那不可名状的怪物似乎也在等待着这个时刻,房间中的寒冷蠢蠢欲动着。
“奴念郞,于桥旁,心意如白霜……”
哒……哒……
那脚步却还是不疾不徐,就如同只是在月色之下欣然地散着步一般。
“此生何时还可诉情长……”
伴随着这最后的歌声,如凋零的杜若花瓣一般,轻飘而哀怨地飘散在月色中,脚步声停了,就停在那扇薄薄的纸拉门前。
男人的瞳孔陡然一缩。
一个庞然巨影映照在拉门之上,翻滚着、蠕动着,说不清究竟是何物,像是一个由许许多多肢体与碎肉拼接成的巨大肉团,更像是一团难以名状的黑暗,舞动着贪婪的触手,等待着捕食一切生魂。
那,那根本不是一个人类,甚至不是人形生物,那就是一团巨大的深渊。
“嗬呃呃呃嗷嗷嗷嗷啊啊啊啊啊!!!”
房间中的怪物似乎感受到了致命的威胁,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愤怒和恐怖,像是一头被困在牢笼里等待宰杀的野兽,发出了临死前绝望的暴动挣扎。
男人瞬间感到自己那种可怕的寒冷再次扼紧了他的咽喉,他的绝望和恐惧已经到达了临界点,双眼翻白,只有一道道血泪顺着结满霜花的脸颊流下。他青紫色的嘴唇终于张开了,越张越大,越张越大,就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塞进了他的喉管,喉头剧烈地颤抖滚动,最终却只是滚落出断断续续的不似人类的诡异呜咽声。
他真的要死了。
房间中的黑暗像是一锅煮沸的粥,巨大的撕心裂肺的尖啸声已经将他的耳膜震碎,鲜血不断顺着脖颈流下。
叩叩。
他翻白的眼球动了动。
叩叩。
敲门声连续两次响起。敲着那扇纸拉门的人有很好的耐心和修养,他敲了敲,又敲了敲,指节触碰拉门表面,很清脆,那声音既不会响得惊吓到房屋中的人,却也不会显得太过轻而怯弱。只不过,那声音却有些拖沓,隔着一扇拉门却也能感受到,敲门之人有些懒散的样子。
“您好,我是警察,正在办案,麻烦您开一下门。”
一个男人的声音出现在寂静的走廊内。房间中充斥着撕心裂肺的尖啸声,他却如同毫无察觉,仍然从容而平静。那声音清亮,温和,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和力,可在这么一个群魔乱舞的夜晚,却显得尤为诡异。
警察……
男人的眼球再次动了动。他似乎想做点什么,可是,那双满是鲜血的眼已是他全身唯一能够活动的地方了。
“不开门吗?应该还没死才对……”
门外之人发出一声疑惑的低语,伴随着那自言自语般的声音,似乎能够想象出,一名青年困惑地抓了抓后脑。
“不开门的话,我自己进来啦。”
是的,这种复古式的纸拉门是无法上锁的,只要他想,随时可以开门而入。
房间中的怪物彻底地愤怒了。它突然地松开了那个躺着的无辜男人,一团不可名状的冰冷腥臭向着拉门猛冲过去。
那男人终于得以恢复呼吸,随即剧烈地咳嗽起来,身体不断地抽搐痉挛着,却不顾一切地翻滚起来,尽其所能从那团蠕动的被褥之中挣脱,连滚带爬地向角落移动。
哗啦一声,脆弱的纸质拉门被拉开了,清澈的月色陡然倾泻而入。男人眼睁睁地看着,月光下,一团散发着腥臭的黑色烟雾翻滚着冲到了拉门前。
然后,静止了。
一切都静止了,黑雾,腥臭,和那撕心裂肺的尖啸声,全部短暂地停下。
打开的拉门前,隐约站着一个身影,并不是什么残破的肢体拼接成的扭曲的肉团,也并非什么巨大的挥舞着触手的深渊,只不过,是一个身材高挑的普通男人罢了。
“您好,我是警察,来办案的。”
那个男人重复道。
下一秒,黑雾爆开了,伴随着山呼海啸一般震耳欲聋的惨叫,凄厉得有如千百只厉鬼正在齐声号啕,那巨大的声浪已经如同实质,险些将男人脆弱的心脏直接撕裂了。
黑雾在房间中扭曲、撕裂,不断地痉挛和挣扎着,那可怕的形态直观地将痛苦表达了出来,就像是一个人被残暴地直接撕掉肢体,散发出触目惊心的绝望。
那个自称警察的男人就这样视若无睹地走了进来,皮鞋硬跟踩在木质地板上,他脚步轻松,甚至十分留意地避开了住客放在地上的物品,就这样缓步走到蜷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住客面前。
借着朦胧的月色,住客看到, 那个男人的打扮既普通又怪异。上身穿着略有些古典的风琴领衬衫,外面却搭配着一件颜色深蓝的浴衣,松松垮垮地以一条腰带束着,长及地面,盖住了穿着皮鞋的脚尖。
他弯下腰,单手撑住膝盖,低头从浴衣敞开的衣襟中掏出了一样东西,递到那颤抖着的住客面前。
“这是我的警官证。”他说。
一个小巧精致的皮本在他手中啪嗒一下翻开,其上赫然印着清晰的警徽图案。
怪谈专案组调查专员,成步堂龙一。
住客的胸膛疯狂地起伏着,那种犹如残破风箱一般的声音再次透出他的肺部。他满是血水的眼眸之中,倒映出月光下房间的样子。
那几乎要将人撕碎的痛苦哭嚎响彻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夹杂着风声呼啸、空气翻腾,四面薄薄的墙壁都呼啦作响,就如同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正试图将那团黑色的雾气攥紧撕碎。房间正中央,那团刚刚险些将他杀死的棉被蠕动着翻滚着,像是一滩垂死挣扎的肉泥,其上不断鼓出一个个篮球大小的凸起,仔细一看,就发现那竟然是无数痛苦扭曲的人脸,每一张都眼眶深陷,大张着嘴巴,发出无声地哭嚎,就如住客方才濒死时一般无二。它们不断向着被褥表面冲击,似乎拼了命也想挣出那棉被的束缚,却只能一次次地撞上被子表面,然后被弹回,就如同那柔软的被面是世上最坚固的牢笼一般。
住客不禁浑身冰冷,背后已被冷汗浸透。他双眼直直地盯着那床诡异恶心的棉被,丝毫不怀疑,如果面前这个奇怪的男人晚来一分钟,他就将会变成和被褥之中的痛苦脸孔相同的下场。
“救……救…………”
他嘴唇翕动,喉咙却像是已经破败不堪,发不出完整的人声。
与此同时,半空中那正在与黑雾纠缠的无形之物突地收拢,黑雾再次猛然爆散开来,痛苦尖啸的声浪顿时更上一个台阶。
面前那个身着和服的男人像是才听到这声音一般,终于皱了皱眉,侧头,用手掌拢住一边的耳朵,又凑近了一些。
“您说什么?大声些可以吗?这声音太吵,我听不清。”
“救……”
无辜的住客下意识张口,想要重复那无意义的音节,但再次被那毁灭性的声浪淹没了。
那和服男人侧头等待无果,有些莫名地抓了抓后脑勺的黑色短发,让那尖锐的造型看起来蓬乱了几分。
“不说了吗?这样我吃不到啊……”
他有些困惑且略带遗憾地自言自语。
随后,他以轻松的姿态,在那无辜的受害者面前,踮着脚尖蹲了下来。浴衣下摆全部垂落在地,他却不以为意。
那持续走高的痛苦绝望的厉鬼号哭之声终于也使他撇了撇嘴,眉头隐约地皱起,似乎颇为不忍。
“御剑啊,小孩子也怪可怜的。”
他回过头,看着那团扭曲挣扎着的黑暗,声音略有些拔高,似乎,在与房间里某个看不见的存在交谈。
几秒钟后,他颇有些无可奈何地摸了摸后颈,咕哝道:
“唔,你说的倒也对。”
“那么就……”
那男人回过头来,低着头,一边漫不经心地继续摩挲着自己的后颈,一边似乎在思索着应对的策略。
* “处理掉吧。”*
下一秒,这个穿古怪服饰的男人抬起头,正对上住客惊恐的双眼。那张脸苍白如纸,双眼像两团黏稠的死海,或是能吸食人灵魂的深渊,是纯黑的,没有一丝眼白,黑色的如同血丝一样的线条从眼眶处蔓延开来,使这男人的上半张脸整个如同一张碎裂开来的白瓷面具。
那张惨白如纸的脸上,竟然还带着温和的微笑。他说“处理掉吧”,轻松得就好像要把一张废纸丢进垃圾箱。
这句平淡的话语,其中竟像是包含着某种神秘的力量,房间内的风声陡然尖锐,就像是在那一瞬间,有一团巨大的能量在房间中碾压而过。
这一刻,住客已经形容不出那团黑雾发出的究竟是什么声音了,他只平白地认为,如果蜗牛也有声带,当它被残忍的幼儿撒盐溶解时,它自灵魂之中发出的便是那样的声音。
住客的神经终于承受不住,在那一刻,彻底地绷断了。
在他的世界陷入一片漆黑之前,他看到,那团黑雾真的如同被撒盐的蜗牛一般,迅速地溶解在冰冷的夜色之中。
那一瞬间,那好像看到了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地飘落,将天地都渲染成纯白。一对孩童躺在雪地之中,他们脸色酱紫,穿着破烂的单衫,彼此紧紧拥抱着,像是在母胎中蜷缩的一对胎儿。
雪片铺天盖地地落下,落在这对孩童身上,他们一动不动,没有任何声息。大雪很快将他们的身体铺满,一层又一层地包裹淹没,就像为他们盖上了一床洁白柔软又温暖轻盈的棉被。
△▽
……
“先生,先生?”
住客的眉头动了动,隐约听到一个声音。似乎是一个男人的反复呼唤,就响在他耳边。
“先生,麻烦您醒醒。”
男人的声音继续着,像是某种惹人厌烦的蚊虫,不断在住客耳边发出扰人的嗡嗡声。
有一点耳熟……
下一秒住客猛然睁开眼睛,下意识地去摸自己的脖颈和胸口。
还……还活着……竟然……还活着?!
他逐渐露出欣喜若狂的神情,沉浸在劫后余生的巨大喜悦中,几乎是过了几秒钟才意识到,自己正平躺在一床被褥中,他猛地坐起,挣扎着想把那床被子推远,却怔怔地发现,这已经不是他撞鬼时盖的那条被子了。
那条暗红色的诡异的被子,此刻被叠成了个乖巧的小方块,正被坐在一个披着浴衣的男人的身下。
他的视线随之上移,那个穿着和服的男人友善地朝他招了招手。
“您醒了啊,再重新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警署里处理怪谈事件的特派专员成步堂龙一,也就是所谓的‘专业人士’。”
住客瞪着难以置信的眼睛,反复打量着这个不速之客,借着月光,依稀能看出他五官轮廓柔和,眼睛尤其大,在月色下闪着隐隐深蓝的星光。他算是生着一张颇耐看的面孔,却也与寻常人无甚区别,没有苍白如纸的肤色,更无纯黑色的眼眸。
“您肯定也意识到了,”他不紧不慢地解释着,看起来确乎十分熟练:“刚刚经历的呢,就是所谓灵异事件了。”
他脸上带着柔和的微笑,话音也亲切,说话间环顾四周,似乎在漫不经心地打量这间屋子。
“这家旅店闹鬼的凶名都已经传到警署来了,你竟然还敢过来,肯定不是试胆爱好者,就是想要取材的作家吧。”
“也多亏了你,才把这两个狡猾的小鬼引出来。不过下次可注意些,老是去这些奇奇怪怪的地方,搞不好真的会撞鬼哦。”
自称为成步堂龙一的男人很耐心地向他解释着,他不做回答,那人便自顾自地说下去,耐心地不像是个警察,而像是个服务业的从业者。
“……我……我?!”
过了两秒,住客像是突然反应过来,猛地吸了口凉气,惊慌失措地想要表达些什么。
“等下。”
成步堂龙一却突然朝他压了压手掌,示意他收声。
住客立即识相地闭了嘴。
“你说什么?”
成步堂龙一眨了眨眼,侧过头,看向身旁的某处,就好像这房间中真有另外一个看不见的存在,正向他说些什么。
他全神贯注地听着。
“哦,”良久之后,他终于点头,了然道:“原来如此,那还确实挺可怜的。不过,就像你说的那样,留着他们也只是让更多无辜者被害罢了。”
房间中再次陷入了寂静。
“我……”
住客再次试图张口说些什么。
“哦对了。”
那个男人,自称专业人士的成步堂龙一,突然回过头来,自顾自地对他说:
“你刚刚目睹的灵异事件,按照规定呢,是要保密的,一般来说,你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现在就被我抹掉记忆,明天再睁眼的时候就已经忘记今晚发生的一切了。
第二种,就是和有关部门签署保密协议,这种我们不是很推荐,因为嘛……一般人经历这种事,想要保密也是很痛苦的,而且一旦违约,是要缴纳违约金的。”
说到这里,那男人露出一抹无可奈何的笑容,随意地摊了摊手:
“那违约金真的很贵,交不起的话,就只能像我一样,给他们打工还债了哦。”
他笑容和煦,没有说明“他们”究竟是谁,手指却向着房间中的虚空出比了比。
“我……”
住客惊疑不定,刚要开口。
“所以,果然还是选第一种吧?”
那个男人却兀自做出了决定。
“晚安,祝别做噩梦。”
他笑着朝住客挥了挥手,下一秒,住客的世界再次陷入一片混沌的漆黑之中。
隐约间,他听到一枚铃铛清脆的声响,如同平静的水面上陡然绽出的一朵涟漪,倏然扩散于虚空之中。
两个男人的对话声隐隐传入他的耳朵。
“成步堂,你没必要一定向他们每个人出示你的警官证。”一个低沉的男声道:“他们并不会在乎你是不是真的警察。”
另一个男人听后,爽朗地笑了两声。
他似乎不以为意,又有几分羞涩,让听到的人几乎能够在脑中浮现他敦厚地抓着后脑的形象。
“我习惯了嘛!”他笑着说。
△▽
“七月炎炎夏,飞书显花押,竹林朝露化黄花……”
哪怕是深夜,这座繁华而充满机遇的亚洲都市,仍然灯火璀璨。一排排高耸入云的办公大楼,玻璃幕墙上跳跃着密集的萤火,覆盖了星空与月亮。未打烊的商店与娱乐场,都亮着霓虹的灯牌,其炫目与喧嚷,甚至还要超越白昼。
就是这样一座包罗万象的城市,四时霓虹璀璨不息,背后却也有着深不见底的黑暗。肮脏的小巷子里徘徊着落魄的醉鬼,地下室之中隐藏着黑帮和犯罪者,只要有黑暗的地方,就永远有挥散不去的腥臭与腐败的霉味,幽灵随处即是,他们缭绕着,纠缠着,时而互相撕咬啃噬,时而又融合为一,专属于城市的鬣狗和秃鹰穿梭其间,以腐臭和痛苦为食,这些一切的一切,共同组成城市真正黑暗的一部分。
然而,与他们共同融化在这座城市黑暗的……
徘徊在电车轨道附近,会发出“啪嗒啪嗒”声音的半截女人;锲而不舍地询问着路人“我美否”的嘴角撕裂的女人;蹲踞在路灯杆上的佝偻黑影;废弃隧道内徘徊的老人;长着人类面孔的恶犬……
没有人知道这些传闻究竟从何处来,却鲜少有人不知道它们,当路人穿行过夜晚无人的街道无意中加快了惶恐的脚步时,它们也已成为这座城市黑暗的一部分。
怪谈,本就是活的。
没有人知道它们是否真实存在,但它们却永远地存在于所有人心中。
获取在某一个瞬间,一个普通人就会与一段怪谈擦肩而过,只不过那时未曾发觉,回首时突然意识到经历了什么,可也再无迹可寻,只如春梦般无痕了。
那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男人,黑发,身量不算出奇,衬衫外披着一件深蓝色浴衣,他就这样在路上悠然自得地走着,边走边唱着歌。
“奴念郞,于桥旁,心意如白霜。此生何时还可诉情长……”
他歌声婉转,唱腔悠扬,甚至用情颇深,虽以男声唱女调亦不显怪异。他行走在车流与行人的狭缝之中,路过一个又一个街角,许多人看到了他,却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目光在他身上停驻一秒。
或许多年后一个相似的夜里,他们中的某一个人,会突然想起曾与这样一个荒诞的男人擦肩而过,他穿着荒诞的衣服,唱着荒诞的歌谣,荒诞地穿街过巷,那时却只觉寻常。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确定是否真的看到了他。可一旦试图回想他的相貌,会意识到这个古怪的路人变成了一团迷雾,就这样消失在记忆的最深处,只留下一瞬空寂的铃声。
而那个男人,还在继续行走着。
一条蜿蜒的河道穿城而过,两边铺设着宽阔的观光大道,铺设着平整的柏油路与人行石板路,沿河装饰着斑斓的彩色灯管,入夜之时,交相映入水面,如同流光溢彩的颜料倾泻入河中,更似天空中绽放的烟火倒映其间。这河边的观光道路虽是傍晚与清晨最为热闹,但这样静谧而绚烂的光景,也只有夜晚能够享用。
两个男人的身影无端地浮现在河边的栏杆处。他们并肩凭栏而立,看上去,似乎正在远眺静谧的河景。
他们中的一个,穿着一套深红如血的袍子,顶戴黑色丝绸的高冠,既像是某位古代高官,又似哪处神庙高贵的神主,那袍襟无风自动,仔细看去,才知其上深红的纹路不是什么刺绣,乃是一道道活的血线,扭曲蠕动着组成一片诡异的红,一头银丝与其相称,如一道银亮的瀑布,自高冠中泄出,倒悬于笔挺的肩背之上,使他的散发一种神秘而阴郁的气质,而当有人产生想要对其真面目一探究竟的想法时,看到一团缥缈的黑雾面纱之上一对冰冷的淡银色眼眸,却发现,自己想不起刚刚那一瞬的念头了。
这样一个神秘如同画中人的男人,怀里却抱着一团折叠整齐的棉被,平白给他增了一分乖巧与两分滑稽来。
在他身旁,站着一个与他身量相似之人,在衬衫外披着深蓝的浴衣,手腕上晃悠悠地缠着一个巴掌大小的铜铃,一边望着平静的河面,一边悠然而深情地唱着歌。
“七月炎炎夏,飞书显花押,竹林朝露化黄花~
奴念郞,于桥旁,心意如白霜。此生何时还可诉情长~”
一曲唱罢,他向前两步,倚靠在河边的围栏上。他抬起手腕,仰着头,旋转角度打量着那枚悬吊着的铜铃。铃铛崭新明亮,下悬一条红丝流苏,像有生命的事物一般,亲昵地攀着男人的手腕。
蓝衣之人似乎对这铃铛颇为喜爱,反复看了一会,更是不舍,却也无私藏之意,仔细地将其从手腕上解下了。那红丝流苏扭动着缠着他的手,真好像是个撒娇的宠物,正舍不得离开主人的掌心呢。
蓝衣人看了,也只是笑了笑。看起来这魂灵本就不是属于他的东西,他要将其物归原主了。
他回身,看了看红衣人抱着被子的滑稽模样,无声地使笑容更深了几分。他没有开口,只是低下头去,拉开红衣人宽大的袍袖,露出一段青白色的骨节突兀的手腕来。
“你……”
红衣人稍一紧张,不由将怀里的被子抱得更紧,想说些什么,或是想要躲避最终却都未施行。
蓝衣男人的手触碰到那截手腕,触碰到那因不习惯肌肤接触而紧绷的人,平静地、若无其事地、仔仔细细地将那铃铛的红丝绳缠在那人腕上,打了个精巧的结。红衣人只是微微移开目光,就如同害怕被对方认真的面容灼伤双眼一般。
而后,蓝衣男人只是亲切地拍了拍那红衣人的手臂,就这样收回了手。
直到他转回身去,那银色眼眸之中流转的视线,才终于能够落回他身上。
“你……”
红衣人第二次试图开口,可那话语在他口中兜兜转转,他嘴唇微微蠕动,似乎不断变化措辞,最终还是没能将那他想说话讲出。
“你就要一直反复唱这几句吗,成步堂?”他的声音听起来十分平静,可在熟悉他的人耳中,那意味着一种拘谨。
被叫做成步堂的男人转头打量了他几眼,那双深蓝色的眼眸突然变得明亮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本来的状态,他若无其事地笑道:
“下面的歌词我忘了——这是我路过磨小豆桥的时候,听一位女士唱的。”
你说的那位女士恐怕是……
红衣之人的神色顿时变得有些复杂。
“下次如果再遇到那位女士,麻烦你联系我。”他有些无奈地说。
成步堂龙一颇有几分爽朗地笑起来:
“御剑还真是尽职尽责啊,今年的最佳阴司奖是不是又要收入囊中了?”
御剑怜侍显然不能适应来自这个男人的打趣,他皱了皱眉,似乎想要为自己辩护一句,却听那男人继续道:
“虽说除去厉鬼是为了保护无辜生者,却也没有做得太绝的必要嘛,有时稍微留些余地,不是为了其他人,而是为了我们自己哦。”
御剑怜侍微微有些惊讶。他是第一次从这个看上去有些懒散的男人口中听到“道理”,他望着成步堂龙一线条柔和的侧脸,成步堂龙一却望着湖面,深蓝的眼眸中没有一丝波澜。他第一次没有对他所不认同的观点产生反驳的念头,只是默默地将这句话记在了心中。
成步堂龙一是怀着善意提醒他的,他想。
或者,这句话能够帮他把这个莫测如深海的男人看得再透些,他又想。
“御剑那边的工作最近很忙吧。”成步堂龙一仍然望着水面,任斑斓的夜灯为他的面孔镀上一层温柔的光晕:“都来找我这种孤魂野鬼帮忙了呢。”
“成步堂……”御剑怜侍的双眉明显皱得更深了,有那么一个瞬间,他的不满快要让他忘记了原本的犹豫:
“你知道我不愿听你这样自称。”
他声音低沉,其中压抑克制着翻涌的情感——似乎愤怒,又像是内疚,抑或难以言明的心痛——任谁也无法相信,这些情感可以被与一个如同冰霜铸就般严酷的阴司相联系。对于一个掌管生死阴阳而近乎神明的存在来说,任何情感都应该是多余的。
成步堂龙一却不以为意,他回身,背靠住河岸的栏杆,轻松地微笑着,终于将他温柔却让人感到几分淡漠的目光投向他的搭档。
“我说的只是个事实而已嘛。御剑,你不会还对那时候的事耿耿于怀吧,已经过去了很多很多年了哦。”
他语气虚浮,话的内容也模糊。很多很多年,听起来,就像是粗疏的他已经将那漫长的岁月淡忘了。
“我……我想我很难不。”
那红衣的阴司低下头,丝丝缕缕的银色自他肩头滑落,流淌着丝绸一般的光泽,恰好将他冷峻的面容上流溢的情绪遮掩。然而,他轻咬下唇发出的低沉的话语,其中有如藏在深海之中的火焰的情感,却隐瞒不过以“言语”为食的厉鬼的耳。
“御剑,我记得我已经说了很多次,那是我自己做出的决定,你虽然是我做出决定的原因,却没必要为我做出的决定负责啊。”
成步堂龙一摊开手,本就松垮的深蓝和服敞开,就如同想要一次展示自己真诚而平静的心。
“更何况,在我看来,那实在是没什么。”
他微笑着,在御剑怜侍面前,眸光清澈得全然不似一个幽魂,然而,那对荡漾着温柔水波的双眸内,却映照出一张满是难以置信的愤怒与悲怆的面孔。
“没什么?你管这个叫没什么?你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吗?!”
魂铃被它所系的手腕带动,发出一声清脆的振鸣。不知为何,路过的行人的脚步都有一瞬停顿,随后又神情略显恍惚地继续行去。
御剑怜侍却不依不饶:
“你……你跳下冥河,挣脱轮回,永不超生,游荡人间做厉鬼,只为了……”
他强势的质问突然被一个更加坚定的声音打断,成步堂龙一在他之前,将这句话彻底地补全:
“只为了不以一碗孟婆汤忘却我战死他乡的好友,那个我此生最珍重的人。”
御剑怜侍哑口无言。
他淡银色的眼眸微微瞪大,其中忽有一线金色混入,为他全无生机的面庞平添了一种难以言明的活气。他的眸光闪烁了一下,最终还是皱眉低下头去,语气轻如叹息:
“在冥府,就算生前最罪无可恕的人,死后也不至于受永世不得超生的刑罚……你……你本应忘记我,去寻找来生的幸福的。”
说罢,他闻听魂铃轻轻摇曳的声音,微一怔,意识到,成步堂龙一握住了他的手臂。
那个男人的声音仍然如方才一般坚定,他眼中那点星火,一如生前一般灼人:
“去往来生,去往没有你的来生吗?御剑,你难道不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你口中的永世不得超生,在我这里的意义是,可以永远留在这世间陪伴你。”
御剑怜侍彻底凝固了。他当然从未想过会得到这样直白又热忱的回应,而几百年的时光就那样过去,愿意接触他冰冷如同尸体的身躯的,愿意用眼中不息的光火照亮他眸中黑暗的,愿意永远陪伴在他这个不祥之存在的,始终就只有这个男人一人而已。
慢慢地,他再次低下头,沉默良久,突然地失笑了。
那一瞬间,成步堂龙一仿佛从他将开未开的嘴唇上读出了一句“真有你的”,最终,却还是被替换成这样一句轻叹:
“……因拒绝喝孟婆汤而一跃跳下忘川水的人,两千年来还没有第二个人。”
成步堂龙一再一次露出笑容。谁又能说那微笑之中没有几分得逞的狡黠呢:
“有什么不好的?至少我还可以在磨小豆桥上唱着《杜若》等你。你就当我是在为不愿意被消除记忆而偿付违约金吧。”
《杜若》,分明是那磨小豆桥上的厉鬼唱来思念远征他乡的情人的吧……
御剑怜侍的嘴角挂上一抹苦笑,他刚要以此句打趣他的好友,就毫无征兆地怔住了,双眼难以置信地睁大,浓郁的金色一瞬间涌入那淡银色的眼眸,使其明亮如同两轮满月一般。烫烫阴司竟抱着一床被子僵立原地,身周那如扭曲的红色血线忽地全部扩散开,化成一团血雾,如同少女羞红的脸颊。
明知道已经没有了鲜血那种东西,那一瞬间,御剑怜侍却产生了一种热血涌上脸颊的错觉。他咬了咬牙,迅速将头扭向一边,用力地攥住了一边宽大的衣袍。
“……谢谢。”
不知为何,他喉头上下滚动良久,却只艰难地从喉头挤出这样一句意味不明的低语。
此时,成步堂龙一却已若无其事地转回身,双肘支在栏杆上,垂坠的和服布料垂下,露出其中的白色衬衫袖子。
闻听这句意味不明的感谢,他忽然仰起头。
伴随着轻微的“咕噜”一声,一团黏稠的漆黑突然自他眼中翻下,覆盖了原本明亮的眼眸,使那双眼陡然变成一对吸食灵魂一般没有眼白的无底洞。
自那双眼周围,一道道如血管一般的黑色的细线陡然蔓延开来,那一瞬,阴寒森冷的气质终于不再别掩饰,一种独属于厉鬼的凶煞之气泄出。
下一秒,无论是黑色血管还是纯黑的眼珠都再次被吸收,成步堂龙一露出一个颇有些受用的笑容,眼神含着意味深长,悄然看向身侧的好友。
“既然感谢我,不如快些把这次的报酬结清吧!”他爽朗地笑着。
御剑怜侍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饱含纠结情感的话语已成了他人腹中餐,深吸了一口气,无意识地深深皱起双眉。
要来了吗……
这个每次来寻找友人帮忙都会最终经历的环节,这个他甚至不知是畏惧还是期待的时刻——是的,这个世上恐怕再不会有人如他一样,会因为要讲一句感情充沛的真话而感到畏惧或期待了,因为也再不会有一个人像他一样,能将一个羞耻的秘密,一个甚至已经不是秘密的秘密,隐瞒几百年。
“我……我…………”
御剑怜侍的喉头滚动着。那句话,他包裹在深海中的火,几乎已经到了唇边。
魂铃发出簌簌的轻响。是悬挂着它的手腕在不自觉地微微颤抖。
“你是我无可替代的挚友。”
御剑怜侍突然地改了口,这句话如同打开了某个蓄水已久的水库的闸门,他所积蓄的勇气,所积蓄的冲动,都迅速地流失了,看上去,就连本属于阴司的骇人的气势都散去了几分。
留在他深深蹙着的眉间的,只剩下委屈与羞赧。
成步堂龙一的双眼再次被浓郁的黑暗覆盖了,黑色扭曲的线爬上了他的脸,他就这样笑了,不知为何,那几乎已不像人的面孔上,却能看出几分的意味深长。
“这句话好像在一百年前就已经品尝过了呢。
下次,可要让我尝尝你新的心声哦,我的‘挚友’。”
伴随着这句话落下,一切都倏地遥远了。
一个夜跑的少女自马路对面跑过,她好像看到了什么,下意识偏头望向马路对面的河边,这时,忽有一辆黑色车从她视线前驶过,短暂地阻挡了她望向对面的目光。
等她再将注意力重新转回时,却发现,对面只有人行道傍着静谧而绚烂的河畔夜景,寂寂无声,空无一人。
隐约间,她好像听到了一个男人悠扬婉转却不哀怨的歌声,如杜若花瓣一样,悄无声息地飘落于夜色之中:
“此生何时还可诉情长……”
△▽
深夜,某栋靠近商业区的公寓楼内,近几年以连载于期刊之上的怪谈小说小有名气的作家A氏,缓缓吐出一口浊气,苦恼地趴伏于桌面之上。
他近期有了一个烦心之事。
他感觉到,自己好像真的撞鬼了。
A氏原本最擅长的便是取材于古代怪谈笔记,近些年已将传统怪谈翻遍,灵感逐渐枯竭。恰逢此时,他听闻西郊一座仿古旅社中有了闹鬼的传闻,尽管他并不相信真有鬼怪存在,却也认为这是一个收集素材的有机会——那间旅社据说许多家具都是古代遗留,夜幕降临时,寒气逼人,阴森恐怖,真如恐怖小说中走出的一般。
A氏便趁着周末无事,独自一人前往这间旅店取材,谁知当晚果然有些古怪,他依稀感到夜晚极其寒冷,半梦半醒间仿佛看到了鬼魇,入睡之后噩梦连连,醒来时却全部记得,只模糊地在他心头留下了恐怖的阴影。此后连续数日,他都感受到浑身酸痛乏力,双眼疼痛难忍,喉痛沙哑难以成言,甚至每每在夜里不敢钻入床褥,只觉有一股极端阴寒的气息自被褥中透出。
他想,莫非,他真的招惹上了那旅社中的鬼魂?如此是否需要找“专业人士”一探究竟呢?
正在他苦恼之时,手机铃声毫无征兆地响起,将他吓了一跳。来电者原是责编B氏。
B氏也是一名恐怖怪谈的资深爱好者,他虽是A氏的工作伙伴,同时也是平日里经常讨论怪谈的好友。
A氏接起电话,果然是B氏的声音自听筒那头传出:
“小A啊,我刚刚在网络上看到了一则怪谈,感到十分有趣,正想分享给你呢。”
A氏此刻正在考虑找“专业人士”驱鬼的事宜,目光望向不远处繁华的商业街区,回答得有些心不在焉。不过好在B氏并不以为怪,继续道:
“我听闻,自很多很年前,就有人说自己碰见过一个身着蓝色和服的男人,他往往会出现在有烦恼或者心事的人身边,以能够给那个人提供帮助的姿态存在。
比方说,如果你丢了重要的东西,他或许会以警察的样子出现,如果你不小心犯了案子,则会在街边忽然见到一家律师事务所。
不管这个男人以什么样子出现,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非常执着于给撞见他的人出示他幻化出来的身份证明。
传说,他非常善于伪装自己,谁也不能立刻就看出,这站在自己面前的竟不是一个活人。
有人向他表露了自己真情实感的苦恼,就会发现这男人转瞬之间就不见了踪影,自己只不过是站在街边,自言自语罢了。但回到家中,却会惊喜地发现,自己丢失的东西找回了,自己犯下的案子解决了,天下竟有如此神奇之事。
可是,若讲了假话,或是有所隐瞒,亲属恐怕便要在近些天内,找到此人被挖去双眼的尸体了。
有人说,这厉鬼实则是以言语为食的,真情实感的话语他最是爱吃,因此吃罢便帮人解决了困难作为回礼,可谎言的味道最是难以下咽,不如一对贪婪的眼珠子来得鲜美……”
B氏说得兴奋,也不顾A氏冷淡的态度,一股脑便将这故事讲完了。说完之后,才隐约察觉今日A氏似乎有些异常:
“小A?你在听吗?
小A?这么没有反应啊?
小A……?”
B氏的声音仿若风中的串珠,一粒粒地遗失了,越来越远,越来越远,A氏握着手机的手慢慢放下了,他呆呆地望着对面写字楼上的一块霓虹的招牌,古旧的形式,却以诡异的彩色灯管点缀,透着一股森森的鬼气。
A氏彻底地僵住了。
那块霓虹的招牌上面赫然写着一行字:
专业解决各类灵异事件——成步堂怪谈事务所。
END.
缓慢地结清欠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