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御】剑阁来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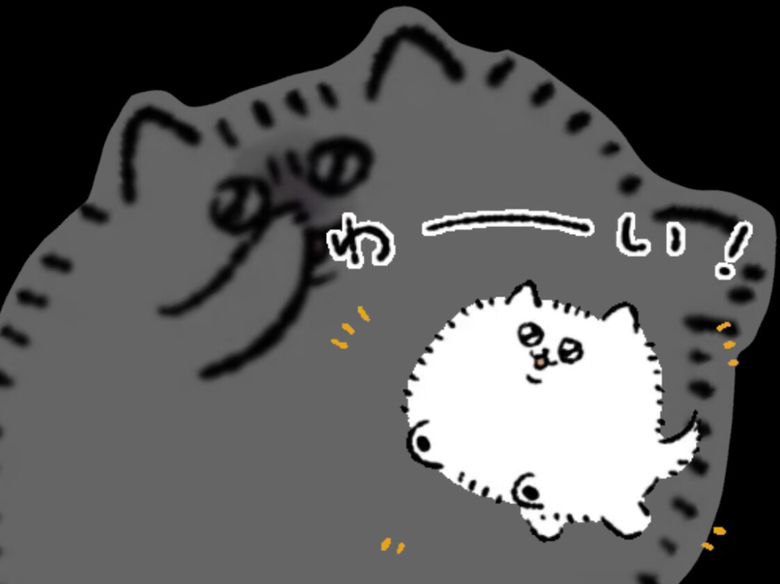
意想不到的武侠pa竟然真的能成
为了契合语境,本篇将角色名全部本土化
01
喻剑曾两次送陈步堂上剑阁。
第一次,顺江而下,七月过洞庭,八月到潇湘,正赶上第一场秋雨,竹林间一片肃杀景象。
陈步堂说,好久没嗅过竹叶的清香味了,二人便轻装下马,步履穿过斑竹林。只见青翠浓淡,竹叶飘飞,夹着雨腥的风穿梭而过,耳边潇潇声不绝。
花中有四君子,唯竹最是险峻锋锐,雨后拔节,杆杆挺直,节节冲天,若心有剑意,入了竹林,便是入了刀剑丛中,战意酣然。
兴味浓时,陈步堂问喻剑可曾听说九疑泪竹。喻剑不答,任由他讲故事。
陈步堂便自顾自讲,湘水去岸三十许里有相思宫、望帝台。舜南巡不返殁葬于苍梧之野,尧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思恸哭,泪下沾竹,文悉为之班班然。
这故事本是《太平御览》所载的,被他添油加醋地讲来却也有趣,正讲到意气风发之处,前方碰巧见一竹倾倒,枝叶尽落,陈步堂将其拾起,作长棍在手舞弄一番,搅得林中竹叶翻飞,好不潇洒。喻剑向来不善言辞,看在眼中,心中有万般爱意,也只有双眸晶亮。
陈步堂将手中竹竿上斑痕展示给喻剑看,笑言道:
“这潇湘万顷泪竹林,斑斑皆是斯人泪。喻剑,我此去剑阁,蜀道峥嵘,难比登天,我若不还,你可为我哭?”
喻剑不回答,轻笑一声,以手接住飘落到眼前的一片竹叶,陡然以暗器之势射出,破风声急,至那人耳边,他猛一扬手,竟将其接于双指之间,只扰动鬓角一缕青丝。
陈步堂不回头,将那片竹叶夹在耳侧,忽然畅快地笑起来,踏起轻功,快意恣肆在竹林间穿梭,大有竹杖芒鞋轻胜马之意。喻剑也笑,不甘示弱地运起轻功,紧随其后,两人如一对翩翩雨燕,穿梭于满天竹叶细雨中,知己之心,无需多言。
须臾出了竹林,两人站在驿站,竟都片叶未沾身,只有陈步堂耳侧那片竹叶,仍旧好好地夹着。
那时他们年少,不懂这世上有许多事是不可谈及的,诀别便是其中之一。
喻剑与陈步堂在驿站住了三日,期间秋雨又起,喻剑也不急走,只留在驿站陪陈步堂,两人夜夜把酒,只字不提践行,但心中却也清楚,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此后分道扬镳,下次见面,当不知何时了。
雨停时,两人也分好了行李,站在驿站口,喻剑需北上,孤身重走来时与挚友同行之路,一路物是人非,不知又有几番惆怅。陈步堂需南行,穿巴峡过巫峡,行过险峻异常的蜀道,蹚过一池又一池的秋水,巴山雨,巫山云,夜夜思君,夜夜不见君。
但他们还是不提分别。少年心性,还不知真正别离的滋味。喻剑只道,此去再向南三十里,便是巴县,夜雨湿重,仔细多添衣。
陈步堂从袖中掏出一柄泪竹骨的折扇,说是他那日在林中拾得的那柄竹杖所制,三天时间,来不及细细打磨,留予故人做个念想。喻剑握在手中,只觉得那桐油还未干,带着友人手掌温度,展开扇面,一片空白。抬头欲问,却见那蓝袍身影已经远了,口中唱着: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及至此刻,二人竟仍一字未提别离。
九日后,喻剑过洛水,在途中流听闻友人讯息:
恒山陈步堂,在剑阁大会众目睽睽之下使出一招魔教功法,从此江湖之中,人人得而诛之。
此后一年,音书俱绝,生死茫茫。
02
喻剑买下长安这间宅邸时,年方十九岁,荫补大理寺右扶风之位,年纪轻轻,便成为官居五品的“大人”。卖家口若悬河,将一间三进的院落说出了花,先夸风水宝地,再讲格局精巧,最后带着小喻大人来到中庭一颗合抱粗的大梧桐树下,指着那郁郁葱葱的树梢道,人道是良禽择木而栖,这梧桐最是有灵,能招引来凤凰,喻大人若是买下这宅邸,这中庭的梧桐树,可就能为您招来贵人啦。
年仅十九的小喻大人微微一笑,他虽生着一张俊秀脸孔,却是幼年习武出身,肚子里该有的傲骨一根也不少,至于什么凤凰什么贵人,他是一概不感兴趣,他只看上这宅邸距大理寺最近,且质朴大方,故而选中。
谁知,贵人不贵人的不知道,这梧桐树,还真给他招来了个“怪人”。
那日他在窗边读书,只听得窗外风声作响,隐约有脚步之声,再听时,只有窗外梧桐的枝丫,发出微微的响动。习武之人心明眼亮,耳听六路八方,不会漏过一丝奇怪之处,他心下存疑,立刻打开窗户查看,却正和蹲在树上的一个蓝袍人影看了个对眼。
那蓝色身影也吓了一跳,想是不料这家的主人会突然开窗,此刻他正顶着满头凌乱的梧桐叶,蹲在枝头装鸟,瞥见窗里的主人,小小的惊呼一声,丢下一句“打扰”,便运起轻功,真如鸟雀一般飞走了。
喻剑心下惊疑不定。听声音,这不速之客似乎是个与自己年纪相仿的少年人。
要知道,当下的江湖与朝廷,乃是分立制衡的局面,江湖遍布大江南北,颇有自己的势力,朝廷虽有兵马却也难约束,而朝廷稳居中央,江湖的势力也伸不进京城长安来。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个“江湖不入朝堂”的规矩,讲的便是江湖儿女不得私自入京,即便入京,也必得装作寻常人模样,不可私自动武,更不可干预朝廷的运作。而今这少年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使出轻功,还飞进朝廷命官的私宅,岂不是大罪?
惊疑之间,隐约又有几道身影掠过,似乎追着那不速之客去了,竟似乎是追兵。喻剑不及细想,趁着那蓝色身影还未跑远,大喊一声“站住”,翻窗便追。
这一追便是十年。
那一日,喻剑追着那落到他梧桐树上的人影,一直追到日近黄昏,中途他们已将所有追兵都摆脱,喻剑却还不依不饶,定要知道这在京城动武动到大理寺头上的大胆贼人的真面目。夕阳之中,只有两道身影还锲而不舍地在屋舍上翻跃着,一整日也未能分出个高下,而他们的身形,显也比最初迟缓得多了。
终于,那蓝袍人率先撑不住,停在一处树梢上喘着粗气,回身委屈地喊道:
“阁下,别追了好不好。我与你无冤无仇,只是踩断你家梧桐树一根枝丫,何至于追我至此啊!”
小喻大人小小年纪,却已有了大理寺要员的肃穆,皱眉回道:
“你在京城动武,缉捕你乃是我大理寺的职责。”
谁知那蓝袍人听了竟更加委屈:
“我哪里有动武了,只是在逃命罢了!我被人追杀,难道还站着不动吗!”
喻剑也愣住了。那少年的委屈丝毫不似作伪,他有些尴尬地侧过头,一声轻咳,继续问道:
“你未动武,那他们又为何追杀你?”
这下轮到那边的少年苦起一张脸。
少年原来名为陈步堂,少时便是孤儿,幸而遇到恒山掌门千寻,收他在身旁做了第一位弟子。
谁料,师门不幸,千寻掌门前几日死于内斗,恒山派内部乱作一团,陈步堂孤身出逃,一路上躲避着追兵和各路宵小,欲到京城为师傅的死寻个公道。
说到这里时,两人已经坐上街边酒馆二楼的雅座,听到陈步堂咬牙说欲寻杀师的真凶报仇时,眼圈真的红了,喻剑也不知怎的,竟也心窝发烫。他自幼失怙,生父也是武林人士,及至今日,真凶还未探明。
“莫说动武了……”可说到这里,陈步堂又泄了气:“我根本就不会武。”
原来千寻虽年纪轻轻,为师却严格,教训学生,一定要从提水桶走梅花桩练起,练了几年小有成效,这才开始练轻功,等到轻功略有所成,陈步堂已然十八,终于练起那本恒山不传的秘籍。
上半部秘籍中,只教了一件事,那便是如何从对手各个关节的运作趋势、甚至是眼神之中,猜出对手的招式也意图,陈步堂乃是个中天才,在这方面天资过人,不到一年,便练成了个心明眼亮的“快手”,只要看到敌人微一动作,他立刻就能做出反应,或闪避或拆招,总之,莫说普通习武之人,就算是师傅千寻掌门,也别想轻易打中他。
终于学到下半部,他满心以为终于能够学到武学的招式,谁知,天不遂人愿,千寻掌门就那样西去了,只留给他半部艰深的功法。
话至此处,酒过三巡,蓝袍少年苦恼地伏在桌案上,头上的黑发都无所适从地蓬乱着。
对了。他突然起身,眼睛又亮起来。阁下,还没问你姓名呢!
喻剑沉默片刻,回复道,在下姓喻名剑,供职大理寺。
“喻剑?好名字!”
一个剑字,让蓝袍少年的眼睛再度明亮起来。
“令尊一定对阁下有很高的期望,希望阁下能成为一位心中有‘剑意’的大侠!”
这是喻剑第一次听到剑意这个词语。他的心突地漏掉了一拍。
“一派胡言。自古江湖不入朝堂,我自是朝廷命官,怎做‘大侠’?”
“非也非也!”那少年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什么江湖不入朝堂,这才是胡言乱语!喻剑你可曾听说,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无论做大官还是做大侠,无论跻身庙堂还是江湖,都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才是!从这一点上论,庙堂还是江湖,有分别吗?”
喻剑愣住了。这句话像一颗陨星,发着滚烫的光火,坠入他心田,留下一个深深的烙印,此后十余年,每每思及此,必有余音回响。
陈步堂还说,他喜欢“剑”这个字,虽然他不会用剑,但剑也不一定要握在手里。
他说,武林的总坛就在蜀中剑阁,那里山高水远,蜀道难比登天,寻常人去不得,只有武林精英中的精英,每逢八年之际,汇集于剑阁之上,举行大比武,以此来选举新一任的武林盟主。剑阁大会是每个武林人心中的梦,对于武林人士来说,上剑阁比武,无异于进京赶考一般。
陈步堂又说,下一次的剑阁大会是在三年后,有朝一日,他必定要登上剑阁,为师傅洗冤,为师门争光。
“然后呢?”不知不觉间,喻剑的眼睛也亮了起来,他似乎在期待着什么,就好像期待着从这与他年纪相仿的少年身上,看到一个已经早夭的自己。
“然后……”那少年挠了挠乱糟糟的后脑,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然后,如果我真能当上武林盟主,就要改革武林,让江湖不再是此前纷争不断的江湖,朝堂也不再是此前孤立无援的朝堂。”
“可是,就算你能位至盟主,只有武林那一方的努力,没有朝堂那一方的配合,你的理想还是实现不了。”
喻剑口中说着“不能”,眼中的神采却一分未少。
陈步堂也笑了,他盯着喻剑那双年纪轻轻便锐利如鹰隼般的眼眸,对方眼中的光彩,不知何时,竟也在他眸中闪现了:
“说得也是,看来,还需要有人在朝堂之中应和我才行。”
天穹之上,满天星斗,倒流河汉入了两个少年的杯盘,星星点点如同故人眼眸。他们相顾无言,亦无需多言,仅仅一碰杯,便将终身定在这杯酒中。
三年,陈步堂与喻剑说过很多很多话,喝过很多很多酒。
陈步堂说京城哪里都好,唯独没有竹子。他昔日在恒山上的竹林里练功,师傅放养他,早晨把他放到竹林里,他便睡到晚上肚子饿时再回。师傅若是见他身上有一片竹叶,便知他偷了懒,要罚他板子,他因此练就了“片叶不沾身”的绝技。
陈步堂说,诗人里面他最喜欢李白,没人能不喜欢李白,李白的诗酒剑俱绝,“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好潇洒快意的剑客!
陈步堂说,有朝一日,他要成一个不用剑的大侠,专用眼睛盯人的破绽、找人的要害,也能成为不败的传说。
陈步堂还说,有“剑意”不一定会用剑,剑意在侠客的眼里心中。就像“大侠”不一定要武功高,为国为民,自是侠之大者。
……
有时候喻剑想,会否自己当年便是知道了那不速之客的过人之处,才锲而不舍地追赶他一整日的呢?
三年,喻剑眼睁睁看着那个不会武的青年在京城捅了一个又一个的篓子,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仇人,也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传奇。三年,那青年的武技突飞猛进,只靠一双锐利的眼,便达到战无不胜的境地。三年,他们形影不离,彼此应衬,相辅相成,他们的知己之情,也隐约突破了某个界限,抵达了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的羁绊。
终于,三年期满,剑阁大会不日便要举行,公务繁忙的喻剑竟为此告假,不远万里,送陈步堂上剑阁。
那是他们人生中最意气风发的时刻。他们踌躇满志,对未来、对天下,都怀着满心的期待,他们是少年人,少年人不懂世事无常,也从不说诀别。
03
少年不知何谓诀别,明知此行凶险,再见不知何时,临别时偏还要留白。
此时再忆,那一面未着点墨的折扇,究竟是临别时有千万不舍万千嘱托,待落笔才觉多情应留白,还是只觉来日方长,总有一日重逢,不如为未来留些悬念,待到重逢之日落笔也不迟?
喻剑不知道。
他只知道,这一年,那个男人一次都造访过他的梦。
那日陈步堂曾问他,若一去不回,喻剑可会为他哭,如今果然一去不回,只留下一柄留白的折扇,扇骨上斑斑竹痕,像是那娥皇女英的泪,至今未干。
无数次月下,他掏出那柄还未完成的泪竹骨折扇,鼻端似乎还能捕捉到潇湘万顷竹林的一丝清魂。他一次次想,陈步堂究竟是何时做的这柄折扇?那三日之间,他们分明同吃同住,他却从未见过那青年削竹做扇,这一根根扇骨光洁得如琢如磨,显然用心颇深,可他竟到了此时才意识到。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他脑海之中似乎浮现出青年深夜偷偷爬起,对着月光,笨拙而小心翼翼地校准着每根扇骨的样子。
而今轮到他,对着月光,小心翼翼地摩过扇骨上每一寸,在其上寻着故人的掌纹。
这一寻,就不知多少不眠夜。
中庭的梧桐上落了一巢杜鹃,每逢月夜,必对月啼血,扰得人不得安宁。下人要将那杜鹃巢打了,喻剑却将之拦下。
都说梧桐是落凤凰的,而今哪怕是落了子规也好,他只怕打了巢穴,那鸟儿再飞回之时,便要绕树三匝无枝可依。
不如归去,不如归去,那子规啼着,又不知多少不眠夜。
冬去春来,春去冬来,算到此时,已经一载又二月的光景。喻剑从未放弃过寻找故人的讯息,可陈步堂此时已是人人得而诛之的要犯,画影图形贴遍了大江南北的街巷,所谓名门正派,必然像闻到血腥味的鬣狗,追逐他的影踪,只为得到传说中那战无不胜的魔教功法。陈步堂的行迹若那样容易探明,此时便是已死上百十次也犹有余辜。
喻剑明知没有消息,却依然不懈地探听。他相信陈步堂没有死,不知为何,他就是知道那个男人没这么轻易便溃败,他知道陈步堂在逃,同时也在等在找,在等在找那个一举翻盘的机会。
这一年的十月,长安大雪三日,雪堆过了门槛,家家户户都封门不出,城外鸟声绝,城内人迹无,偌大个长安,顷刻化作一片坟。
这一夜的三更,风雪又盛,北风夹杂着鹅毛大的雪片,啪啪地拍着窗棂,单薄的窗纸呼啦啦地响,深及小腿的大雪将窗外映得通亮,喻剑房内只有一盆火碳,毕毕剥剥之声乍响,仿若雪重折竹。
好大的风雪。
他闭眼凝神听,只觉今夜的北风中夹杂着杀意,铿锵有声,直如金铁交鸣,煞气横生。
听着听着,他忽然眉头一动,心下凛然。
北风裹挟来远方的脚步,很急,不只一人,却不纷乱,此时四处都是及胫深的雪,这几人的脚步却没有踏雪时的轧轧声,显然身法极为高明,绝非善类。再细听,一个脚步声最近,跑得最是靠前,却时有时无,显然神出鬼没,听不分明。其余脚步声时聚时散,几次想要追上那前头之人,却都被他诡谲变化的行迹迷惑,再度被甩脱。再细听,前头之人脚步虽说变幻莫测,每次出现,却都更近一些,听上去就好像目标明确,正向这边来……!
习武之人总有极为敏锐的直觉。喻剑忽然意识到,自己心跳已如擂鼓,浑身热血翻涌,额角青筋绽出,他等着,紧盯着那扇被雪映得通亮的窗子,像是将浑身的注意力都凝聚在那一点,所有感官都催至极限。
“啪”的一声。
窗外中庭那颗梧桐树,一根枝丫断裂的声音在此时的喻剑听来如此刺耳。
下一秒,窗子霍然洞开。
呼啸的北风夹杂着片片大雪,猛然涌入,房间内的火炭陡地爆燃起一团大火,窗框上无声爬满了白霜。
一个身影蹲踞在窗框上,一身肃杀的黑衣,蒙面的黑纱上结满霜花,他背对着月光和雪色,与黑夜融为一体,只有那对布满血丝的眼,明亮如同鹰隼,刺破寂静的长夜。
对视只在一瞬之间。
兔起鹘落间,黑衣人翻身跃起,身形矫捷如同鬼魅,猛地捂住喻剑口鼻,与之滚入屋中。几乎便在下一瞬,廊檐上传来脚踏瓦片之声,或许看见目标进了这家院落,却眼睁睁地跟丢了。
几个脚步声在他们头顶的瓦片上徘徊片刻,惊扰得廊檐上的积雪簌簌落下,最终恐怕惊扰了房屋中的“大人物”,像是被夺走食物的鸦鹫,盘旋几圈,终于各自散去。
脚步声远了,吹入窗棂的大雪竟也奇迹般地小了许多。黑衣人若无其事地松开喻剑的口,起身,掸了掸身上雪。
风雪夜归人。
那男人的身形丝毫未变,只是包裹在一身黑衣中,稍显萧条了些,刚在的翻滚之中,他蒙面的黑纱落了,露出棱角愈发锋利的侧颊。相比当时长安少年,他的皮肤染上了风霜之色,下颌上生着一圈潦倒的胡渣,背后背着一把长形之物,其上蒙着的黑布也在翻滚中松散,露出里面的事物,竟不是刀剑,而是一把破琴。
那人抖落衣襟上的雪,低着头,却也不看喻剑。
喻剑只觉浑身的血激荡到无以复加,他眼眶发烫,喉头又酸又涩,浑身簌簌地抖,胸膛剧烈起伏,久久,竟只吐出一句:
“你……你还知道回来。”
“我不是回来。”那男人的淡淡道:“今夜雪重,到喻大人家的庭院避避风雪。这便走。”
“此去往何处走。”“不知。”
“此去何时归还。”“不知。”
那雪夜来客再抬首,只见昔日的挚友拦在自己身前,原本波澜不惊的面孔上,写满了刻骨的情感,愤怒,怨怼,痛苦,还有好多好多不可名状不可思量的思绪,烧红了喻剑的眼眶,也烫伤了陈步堂的眼。他迅速扭头,想要避开那道燃烧着火焰的目光,可是,已经晚了。
“混账……”
伴随着这几乎失态的低声叱骂,喻剑猛地挥出了拳头。这一拳不含任何招式与技巧,仅仅发泄心中那无名的怒火,连凡夫俗子也能够轻易躲过。陈步堂却不躲,他拼着让这一拳挥在他脸颊上,身子陡然前扑,抓着喻剑的肩膀,毫无征兆地与之翻滚到床榻之上。
“喻剑……”陈步堂的声音嘶哑,双手死死抓着故人的双肩。那双手冰冷刺骨,两颊上刚刚被痛击之处却热辣辣地发烫。
还是那双仿若含情的双眼,此刻却无半分缱绻,目光如电,里面迸射出刀剑交接时刹那的金光。
是陈步堂,却已不是他熟识的那个陈步堂了。
喻剑望着那双锐利的眼,像是被摄了魂魄去,一刹那连呼吸都忘了。
“喻剑。”那男人又说:“让我要了你。”
“什么?!”
“我想要了你。”
喻剑猛地瞪大了眼睛,一瞬间只觉气血上涌,耳边嗡鸣,双颊如同火烧,只能咬牙道:
“我若不许呢?”
那男人毫不动摇:
“我来便是为了你。你若不许,我这就走。”
沉默。喻剑用力地咬紧下唇,偏过了头。
“可是……你总要告诉我为什么。”
“因为你爱我,我也爱你。你想要占有我,我也想占有你。”
寂静的雪夜,风雪声突地大了。喻剑听到了自己陡然粗重的呼吸声。
良久,他缓缓爬起身,背过身去,解开自己上身的衣衫,袒露出男人精悍的腰背,在那之上,遍布着学武之人深深浅浅的伤痕,一头银丝如瀑般散落,与那白皙得不似男人的肌肤一并,被今夜的大雪映的发亮。
陈步堂沉默地看着,突地一把将其抱入怀中。
再无需多言。
……
雪停了,只有火盆里的木炭噼噼啪啪地响,还有两具筋疲力竭的肉体交叠的喘息声。
喻剑披上外袍,起身掌了灯,再回床上时,见那男人不知从何处翻出了那柄泪竹骨折扇,展开在手心,细细摩挲。
喻剑道:“你想写些什么,现在可以写了。”
陈步堂只是摇头。
被褥中余温尚存,喻剑再将这让自己牵肠挂肚的男人揽入怀中,无声抚摩那熟悉而陌生的面孔。
月色太冷,此前借着那点冰冷的光辉看这张脸,只觉得棱角分明杀气凛冽,而今在烛光下,竟像是悄然地融化了,眉眼还是那样的年轻,带上几分柔软的孩子气,睫毛很长,猝不及防地一抖,便像是有多情的星子落入眼波。
御剑的手轻轻落于那男人精壮的身体上,指尖小心翼翼地抚过那比一年前更加瘦削突兀的脊骨,抚过一道一道或许曾深可见骨的疤。一道,两道,三道……总共十九道,喻剑都一一地数过去,抚过去,用切切的目光吻过去,深深烙印在自己的心中。
陈步堂沉默地枕在喻剑的怀中,不知为何,喻剑只觉得胸口发酸。
“喻剑……”那男人轻声唤着,如同梦呓:“怜侍……”
“嗯。”喻剑轻声答:“我在。”
“谢谢……”
突如其来的道谢让喻剑心中一紧,他像极了惊弓之鸟,只恐怀中人只是泡影,刹那间便化作一缕青烟消散。
“谢什么?”
“……我没想到,你竟真的愿意委身于我。”
喻剑苦笑。今夜的突变,他又如何能够料到呢。
陈步堂抬头,深深地望着他昔日的故友、今夜的情郎:
“一日夫妻百日恩,喻剑,今生恐怕不能与你结夫妻之恩了,今夜就当是你我的花烛夜,来生我愿为你做姑娘,你一定要娶我,不许纳妾。”
喻剑不易察觉地笑了。烛火轻柔地附在他眼睫间,他那凌厉的双眼竟从未有过此刻一般的温存:
“好说,”他回应道:“但你若没有化作女子,又当如何?”
陈步堂咧开嘴角,露出一个熟悉的羞涩而敦厚的笑容:
“我若没有化作女子,定是因为舍不得喻剑的温柔乡,到那时,只能委屈喻剑再委身于我一世了。”
“混账……”
喻剑低声斥着耍起赖皮的陈步堂,却又忍不住笑起来,他心窝好烫,眼眶好烫,脸颊也好烫,想要推开怀中的男人,手臂却舍不得用力,只能任陈步堂抱紧了他,他也抱紧陈步堂。
喻剑笑,陈步堂也跟着笑,喻剑的笑声渐渐停息,却感到怀中人的笑声有些奇怪,断断续续,伴着深深浅浅的抽气声,渐渐地,淹没在寂静的夜色中。
喻剑突然意识到,陈步堂在哭。
这个男人哭了,尽管没有眼泪,也没有声息,却像一柄生锈的钝刀,已经插在喻剑心头一年又二月,却在此刻才让他感受到那刺骨的疼。
一年又二月,茫茫生死,无迹可寻,多少次冤枉屈辱,多少次险象环生,多少次江湖夜雨,多少次入骨相思,这一载光阴长得像是一辈子,那可悲可叹处,竟似到此时在重重地压到二人肩上。
心痛如绞,寸断肝肠。
04
喻剑曾两次送陈步堂上剑阁。
第二次,已是八年后。八月过洞庭,钱塘江水正高涨着潮水,他们落脚在洞庭湖畔,此时,也是洞庭最壮阔广大的时候。气蒸云梦,波撼岳阳,好大的一盘银镜,堂堂君山落在其中,竟也只如同小小一只青螺。
好一个烟波壮阔的大泽,倾覆乾坤,倒流河汉,不过如此!
八月潮涌时,洞庭湖最是以云雾著称,水汽蒸腾翻涌,使那八百里洞庭尽数笼罩在浓郁如酥的大雾中,沆砀千里,一应俱白,船行其中,见首不见尾,真似到了仙境一般。
车马行至洞庭畔,陈步堂兴味盎然,偏要下马走水路,背着他的那把破琴,载着一坛好酒,拉着喻剑二人上了一艘独木舟。小舟驶入浓雾,便犹如一苇草芥,晃晃荡荡,向那烟波浩渺的洞庭湖心漂去。
四周的浓雾之中,时而隐约有船影经过,也只瞥见只鳞片爪,便耳听苍茫的船号声由近及远:
齐天水,渡人船。
下洞庭,上江汉。
风扯雷,雨来川。
龙摆尾,龟镇潭……
二人盘膝安坐在舟中,推杯换盏,畅谈无碍,天下大势,古今笑谈,无不入杯盘之中,好不快意!
七年,为了这一次的剑阁大会,陈步堂等了七年,他与喻剑合谋,不但暗中将他出师的恒山派权柄握在手中,还与朝廷勾结,欲借朝廷之力,将武林的大权也收入彀中。
他时常说,恒山是俗家弟子与佛门弟子各占一半,掌门虽不一定出家,但也要终身奉道,不得婚娶。师傅年轻时不想做掌门,是因为也曾有一心上人,后来心上人一去不还,这才决心奉道,接管了掌门之位。而今他若能回恒山,便也要接师傅衣钵,终身不娶,做恒山为数不多的男掌门了。
天下已苦江湖纷争久已,习武之人只顾相互倾轧、争名夺利,却不管天下不管百姓。陈步堂此番再上剑阁,不但是要为自己一雪“魔教”的旧冤,更誓要为天下人谋一个能为民作剑的江湖!
笑谈之间,酒意渐酣。陈步堂忽地将那把破琴横于膝上,喻剑心中好奇,从前只听说,陈步堂这些年浪迹江湖,假作卖艺的流浪琴师,莫非这琴技竟也真的学了两手?
思及此处,琴弦铮然而发。
那硬瘦之声,竟不像琴弦拨动,而是弓弦乍响,风声鹤唳,惊飞鸟,动池鱼,刀光剑影之声,皆藏在其中。
喻剑心下凛然。
陈步堂不会弹琴,也不会使剑,他弹的,却是心中铮铮作响的剑意。
山川日月为之肃杀,洞庭悲风与之齐鸣。七年的韬光养晦,七年的卧薪尝胆,七年的潜龙勿用,便要在一朝铮然而发,一鸣惊人!
就连素来冷峻的喻剑,也难不为之热血沸腾。
一曲弹罢,陈步堂意味深长地笑着,望着与他过命的知己,眉若含情,却双眸如炬,问道:
“何如?”
喻剑的双眉紧锁,眼神晶亮,嘴角却含笑意:
“琴技太差,不堪入耳。”
陈步堂于是开怀大笑,拍翻了手边酒坛,霎时酒水横流,酒香四溢,他抱着怀中的破琴,手掌啪啪地拍着琴头,就这样击节高唱: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
05
五月的长安,春风得意,繁花似锦,软红十丈。到处高挂着彩绸与花灯,与一簇簇芍药牡丹争奇斗艳,衣着鲜妍的妇人女子站在桥头,向桥下的船客热情放浪地抛洒着花瓣,高楼上的名伶一支剑舞便博得红绸无数,时时有五陵少年打马飞驰,人声马声吆喝声络绎不绝,好不热闹!
而今日的长安街头,却比往日更加人声鼎沸,不为别的,只为百年来“武林不入朝堂”的规矩,在今日彻底破除了!
以新晋的武林盟主为首,昔日江湖群豪骑着高头大马,自最为气派的北城门鱼贯而入,全城百姓涌上街头,只为目睹往日那神秘莫测的“江湖”。几个年及二八的姑娘手握花篮子自街边跑过,笑着闹着谈着今日的见闻。她们说那前头骑白马穿蓝袍的盟主好生年轻英俊,说他眼波含情,朝人一笑便能勾人的魂;说他好生有趣,其他习武之人腰挎刀枪剑戟,唯有他赤手空拳;说他自剑阁上来,好似神仙下凡、有凤来仪,人都号称“剑阁来客”;又说可惜了这样的奇男子,被簇拥在恒山精灵似的女弟子之间,却无半分留恋之意,而恒山掌门历代都是不准婚娶的。
姑娘们都笑起来,有道是“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这风流的武林盟主,说不定也有他的曾经沧海呢!
这样热闹的盛景,那位已位至九卿、明里暗里推动“武林入朝堂”的大理寺卿喻大人,却选择闭门不出。
近年来他随着仕途升迁,所负责的公务也越发繁重,夜夜剪烛批复公文,早早落得眼花的毛病。这在习武之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之事,好在有一位常年走南闯北的“大侠”,贴心地为他带来了西域人特制的琉璃镜,圆圆一片,嵌着精致的金丝,卡在一边眼窝中,正与他高挺的鼻梁相称,也算不失习武之人眼疾手快的风骨。
此刻他正倚在窗边,漫不经心地听着远处街市的喧嚷,由远及近,再由近及远。他眉眼古井无波,平静得犹如远山,其中的剑意,恐怕只有熟识他的人,才能看得清。
他听着如浪的人声,心中了然。从今而后,江湖不再是此前纷争不断的江湖,朝堂也不再是此前孤立无援的朝堂,江湖将为朝堂所用,成为朝堂的臂使和朝堂的剑,而朝堂又是百姓的臂使与百姓的剑。
浪潮要来了,就如八月的钱塘江,汹涌地奔向瀚海。浪潮之下,朝堂与江湖,不再泾渭分明,而他,还有那位骑白马的“武林盟主”,就是站在浪潮最顶峰的人。
“啪嗒”一声。
极轻细的,如同一只轻盈的鸟雀落在中庭的梧桐树。喻剑笑了,他眼虽有恙,耳力却还如当年那般一丝不苟。他推开窗,正有一蓝袍人蹲踞在梧桐枝头,丝毫没个武林盟主的架子。既不配剑,也不持刀,赤手空拳,春风笑面,亮晶晶的眼睛,年轻如昨日般的面孔,朝他笑:
“喻大官人,已经官居三品了,还住在这破旧宅院内,未免有失身份啊。”
喻剑微眯双眼,嘴角也隐含笑意:
“你有所不知,我这宅院倒没什么稀奇之处,真正宝贝的是你脚下这棵梧桐树。我买这宅邸时,人说梧桐有灵性,能招引凤凰来我阁中筑巢,我还当儿戏,想不到真的招来了,不但招来一次,还招来许多次。就是不知,这凤凰何时才能在我阁中筑巢啊。”
来人哈哈大笑,眼波流转,刹那竟挤出一丝委屈来,赖皮道:
“朝堂都许江湖人走正门了,喻大官人的府邸就不许凤凰走一次正门么?”
喻剑也笑:
“那也要看凤凰愿意与否了。”
“怎不愿!”那来人睁着一对琉璃一样亮的眼珠,一跃而从梧桐树上飞下,真如一只雀跃的大鸟,稳稳落进喻剑怀中:“从今往后我日日要走正门,让人看看,这喻府可并非只有一个主人!”
“人都叫我剑阁来客,谓我从剑阁上来,却不知我是自喻剑大人府上去的,这喻大官人的府邸,岂不也是种‘剑阁’?说到剑阁来客,我可是实至名归!”
于是两个人都笑起来,倚在窗边,靠着书案,紧紧相拥。自彼此的眼中,他们都看到了那年长安的风流走马、潇湘的斑竹带泪、雪夜的凄怆归客、洞庭的击节而歌……他们看到了彼此,看到了彼此的意气风发,也看到了彼此的风流云淡,看到了彼此每一次的凄惶无助,却也看到了彼此如今的成竹在胸。
知己的眼眸里,不但能看到自己的样貌,还能永远地映照自己的心迹。
除此之外,还有剑意。
永恒的剑意,既是剑指天下的意气,又是剑定天下的胸襟。剑意不在剑上,而在真正侠者的眼中。
当他们望见彼此眼眸中那点从不为岁月与世事磨灭的星火与锋芒,他们都露出了会议的微笑。
无需多言。
叮当一声,案上一凉透的茶杯被碰得泼洒,如同浪潮,席卷整个桌案。其上展平着一把做工粗糙的泪竹骨折扇,虽然粗陋,却得主人细心保养,其上的桐油被盘玩得锃亮,斑竹的泪痕已然淡了,泛黄的扇面上题着四个苍劲的大字,乃是“侠之大者”。角落处更有一题款,细细看去,也是四个字,便是:
剑阁来客。
End.
最近一写东西就头痛欲裂,迫不得已,跑回自己的快乐老家,我手癖中的手癖,舒适圈中的舒适圈,我文字表现力和审美的尽头,一口气写了一万多,写得我眼冒金星,虽然是在敲键盘,却也有一种口沫横飞的感觉。。
本篇名为剑阁来客,不知道家人们是否有注意到,全文一共五章,一四章为御剑送成步堂上“剑阁”,二三五章则是成步堂通过中庭梧桐树造访“剑阁”。除此之外,我还倾囊化用了大量的典故和诗句,巴山夜雨、九疑泪竹、雪夜归人、洞庭击节,还有最后的侠之大者,全都是我很喜欢的意象。不但从他们的少年意气写到了波澜不惊,从懵懂写到了事业有成,从相知相识写到相爱相守相辅相成,还写了我期盼已久的很有侠气的4成,也算是不留遗憾啦~
这个文风可能让家人们觉得很陌生,不过这才是我最擅长的文风,本来不适用在成咪这里,但我还是强行写了,总的来说,我写得过瘾了,也希望大家能喜欢T.T、、
另:剑阁来客也是一首歌曲,我写的时候听了很多遍,就留给大家当ed啦~
就这样,头好疼,休息去了,挥挥~
